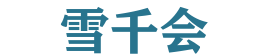福建人真是太容易出圈了,尤其是涉及任何与神沟通的场景。就拿前阵子来说,号称颜值天花板的“世子天团”,再次引发全国乃至世界的关注。专门奔去福建长乐参加完游神的朋友跟我科普:大开眼界!
《烟火人家》剧照
卞芸璐

两个“苦瓜”,非要成家。追看近期热播的家庭群像剧《烟火人家》,评论区里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,便是这句带着同情、爱怜又掺杂无奈的评价。
《烟火人家》是一部当代都市剧,也是一部以家族为人物关系“地基”的女性群像剧。它的故事围绕孟家三代女性展开。姥姥乔海云年轻时是雷厉风行的乔厂长,如今已年逾古稀,但依旧是家中“不怒自威”的大家长。三个女儿孟明玮、孟莞青、孟以安,性格各异、事业成就不同,但都在经历焦灼的家庭和婚姻危机。外孙女辈的李衣锦、陶姝娜年龄相仿,看起来都是衣食无忧、不缺爱的年轻女性,但来自亲密关系的种种考验依旧羁绊着她们……
开篇提到的那句观众评论,便发生在李衣锦决定和前男友周到复合之后。拥有“直升机”式母亲的李衣锦选择了周到——一个原生家庭因父亲暴力和母亲“杀夫”而破裂的年轻人——作为人生伴侣,这不啻于在老孟家投下了一颗小型“核弹”。李衣锦的自我觉醒让三代人的命运齿轮都因此转动。关于母女关系的度量、婚恋选择的反思、人格独立的定义……女性命运的“回响”,在《烟火人家》中震耳欲聋。
女性群像重回“家庭”
在群像构建中为当代都市女性画像,借互文共振映照女性集体命运。这是2015年来,以《欢乐颂》为肇端的一批都市女性群像剧,遵循的共同创作宗旨。从聚焦年龄议题的《三十而已》《二十不惑》,到以喜剧赋格女性成长的《爱很美味》《芳心荡漾》,再到与地域书写融合的《我在他乡挺好的》,一批电视剧迎着女性观众“理想中的自我”书写,用友谊链接不同代际的女主角们,上演了一场场都市漂流记、职场成长记。
但当代女性的人际关系,并非只有“闺蜜互助”一种;女性人生成功的价值标尺也并非只有征服职场一个。人物关系的模式化、随意化,价值取向的单一性,让女性群像剧不再能与鲜活现实共振。都市生活无法逆转的“原子化”倾向,也让观众对荧屏上的家庭“联结”重塑愈发渴望。
当创作者们苦思,什么样的女性群像才更契合现代女性“画像”时,一批重回家庭场景,并没有为时代女性“作传”野心的剧集,闪现出灵动火光。这其中,有讲述“破产母女”携手破局的《生活家》,有以姐妹命运映照都市化进程的《心想事成》,有以人生重启和母女相互救赎为主题的《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》,还有表现游子返乡和与原生家庭再融合的《故乡,别来无恙》。
《烟火人家》则是一部站在女性群像剧和家庭剧交叉口的作品。它收缩了社会辐射面,将女性群像重新拉回家庭场景,以代际关系为核心戏剧张力,强调以性别视角审视亲密关系难题。相比以《浪漫的事》《家,N次方》为代表的传统家庭剧,《烟火人家》不再强调“以小家见时代”的创作取向,而是刀刃向内,把重心放在了女性的自我确认、情感成熟和亲密关系的流动上。相比强调中年焦灼的《熟年》、以苦难打头的《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》等近年的家庭剧创作,《烟火人家》聚焦的是生活轨迹更普通、亲情关系更常态,但却依旧经历成长阵痛的女性。普通女性在成长中遇到的普通冲突、误解,为什么对当事人来说,显得如泰山压顶?这重对普通的聚焦,反而成就了《烟火人家》的典型性。
“好女孩”的成长阵痛
《烟火人家》的孟家三代女性中,乖巧听话、性格隐忍的李衣锦是当代普通“好女孩”的代表。
她有着最普通的成长轨迹,出身工薪家庭,一路按部就班读到本科毕业,离开小地方到大都市求职,做着一份普通的办公室文职工作。她也身处我们熟悉的家庭关系中,有着望女成龙把“为了你好”挂在嘴边的母亲,和沉默如山、有自己世界的父亲。她还有着最质朴的生活追求和纯粹的爱情观,从没想过通过恋爱婚姻跨越阶层,只想找一个意合情投的坚定伴侣,一起共担人生风雨。但就是这么一个严格按照社会时钟成长,也没有“吸血鬼”父母的女孩,却始终在独立人生的迈步上受阻,在婚恋生活中也频频碰壁。
为什么普通的成长路径,没有导向顺遂的人生?《烟火人家》中围绕孟明玮、李衣锦母女俩编织的“中国式母女关系”很值得审思。
母亲孟明玮的人生经历,在20世纪50—70年代出生的城镇女性中,也算得上典型。她经历过匮乏的成长年代,在集体氛围浓厚的工厂奉献一生。因为天生跛足,让她在近关系型社会中遭受议论,自信心匮乏。来自婚姻中冷暴力的创伤,则让她始终处于不安全感和被抛弃的恐惧中。像这样一个长期处于焦虑中的母亲,在输出母爱的同时也夹杂着超出常态的控制。李衣锦从小养成了内生性的顺从,习惯通过牺牲自己的感受和愿望,以维持和母亲的良好关系。
但力的作用总是相互的,与母亲的过度控制相伴相生的,便是女儿迟早要来的反抗。李衣锦的成长阵痛,便与过度的自我牺牲和失衡的叛逆反抗有关。面对母亲过度细致的起居照顾、行程管理,李衣锦感到压迫,但却因母亲的忘我付出而不忍心苛责。为了应对母亲的催婚压力,她甚至找来异性朋友假扮男友,最终既伤害了友谊也让母女矛盾再次激化。
不过,从人格成长角度来看,这种阵痛是必要的。正是在阵痛之中,她意识到逃离并不能兑换自由,自我压抑只会带来慢性抑郁,只有坚定选择并守好边界才可能收获独立人生。也正是在矫正了自己的成长航道后,她才拥有了更平等的视角,觉察到母亲在失败婚姻中的痛苦,并在此基础上达成理解。
如果把这种焦虑控制型的母女关系比喻成一座孤岛,《烟火人家》不仅聚焦了女儿的成长和突围,也拍出了母亲的无声呼救,还表现了母女两人同舟共济逃离“孤岛”的过程。这样一对在中国当下社会具有代表性的母女,她们划出的成长弧光,不乏理想主义,也带启示色彩。
女性命运的隐秘呼应
女性群像回归家庭,不仅为复杂人物关系构建提供了前提,还为女性命运间的互文酝酿了空间。《烟火人家》中,由孟家三代六位成年女性构成的人物关系图,能够氤氲成一组群像,不仅因为其中代际承袭、同辈比照的网状关系,还在于女性人物命运间的隐秘呼应。
单就母女关系来看,《烟火人家》便通过孟明玮、孟莞青和孟以安三姐妹,架构了三种不同的相处模式。
孟明玮和孟莞青是一个对照组。面对强势母亲,孟明玮是言听计从的一个,孟莞青则在年轻时便选择了反抗。不同的母女关系动力,决定了两姐妹不同的人生轨迹,也影响了她们对待下一代的情感模式。孟明玮对女儿的过度控制,孟莞青能成为“梦中情妈”的根因,便藏在她们与母亲的相处模式中。
孟以安则和母亲乔海云之间形成了命运“回响”。
她是三个女儿中最像母亲的一个,同样的能力出众,同样选择了自己的老师作人生伴侣。潜意识牵引着她复刻父母间“模范夫妻”的相处模式,因此在撞破父亲的秘密后,也开始担心自己会重复母亲的悲剧。不过,“回响”不等于复刻。就像乔海云的“外室”身份有强烈的年代印记一样,孟以安在婚姻关系中也有着相当鲜明的现代意识。在时代潮头中博浪的她不受困于“母职内疚”,追求关系平等,最终在亲密关系中找到了平衡。
类似的“回响”关系,还存在于李衣锦和母亲孟明玮之间。相似的女性,因时代不同、独立意识程度有别,踏上了不同的命运起承转合。《烟火人家》以家庭关系为依托,为女性命运的复调“回响”找到了合适场域。
也许是为了激化戏剧矛盾,与女性群像的熠熠生辉相比,《烟火人家》中的丈夫们则成群溃败。他们或嗜钱冷漠,或自私油滑,总体保守愚钝。即便因人格和品德缺陷屡遭家庭危机,他们也毫无成长迹象。这样的男性形象可能不乏现实灵感,但具体到艺术创作中,就需考虑典型性问题。如果能在男性角色的内在逻辑、成长弧光上也有对应着墨,《烟火人家》塑造的家庭群像就能更平衡、圆融。
(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 与传媒学院青年教师、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访问学者)
来源:文汇报